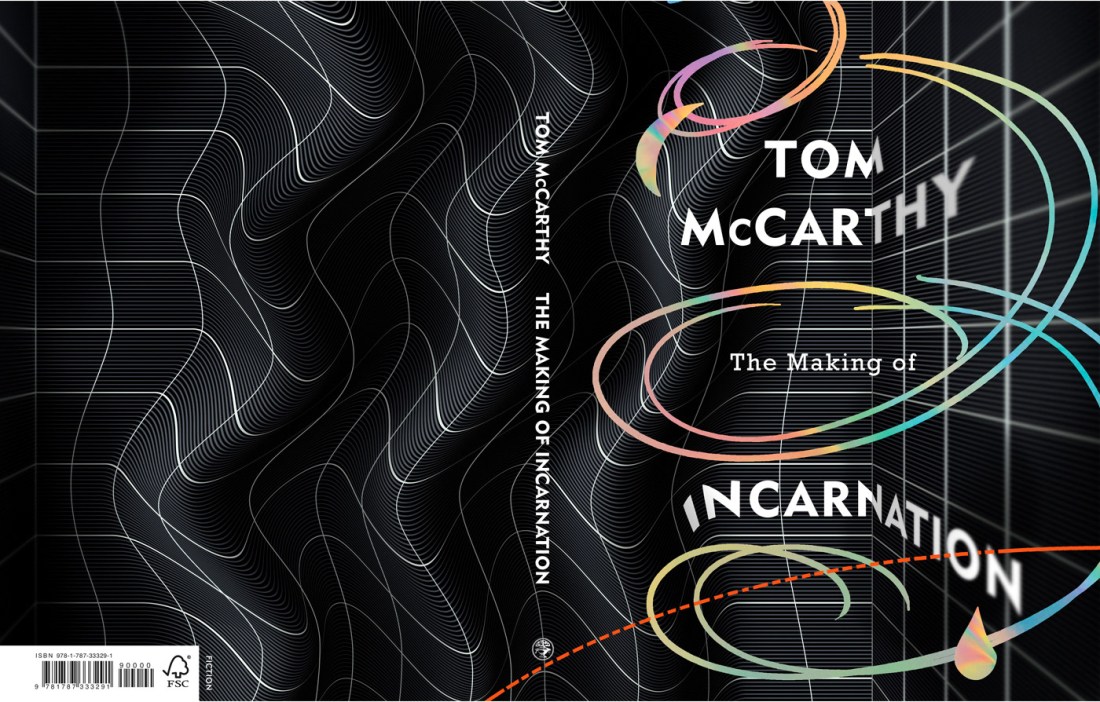英國小說家湯姆・麥卡錫二〇二一年推出的《化身製作記》(The Making of Incarnation),以長篇小說的篇幅,思考科技和真實之間的關係。麥卡錫認為,文學與科技之間的關係,早是一股暗流1 。而文學本身,甚至只能在我們直面自己正是嵌入於各種系統和網絡中,以至與「真實的」自己脫節這一事實之後,方有誕生的可能2。他所指的系統與網絡,可以是語言、科技、基建等,而這統統都與我們受其中介相關。來到《化身製作記》,這一套關於中介的文學思考,則把目光轉往了動作捕捉(motion capture)、虛擬真實(virtual reality)等科技前沿範疇,處理人與時間及動作的關係。
在時間流中捕捉動作
與其說《化身製作記》以角色驅動故事,小說反而多以業界和公司的需求,驅使員工行動。在故事中,居於中心的公司名為Pantarey,專職研究動作及動作捕捉。一家電影製作公司希望製作一部劃時代的新太空歌劇巨著《化身》(Incarnation),規模如同星戰系列,因而請來Pantarey,為電影中的電腦合成影像作顧問。這些影像顧問工作,包括處理戲內各種角色的動作模擬,異星種族的奇行姿態,以至太空船內的光線追蹤(ray tracing)。
動作捕捉的特色在於,它將一些本來自然的動作,從日常的時間抽取出來,加以記錄、分析,從而蒸餾出特定的舉止系列。這些系列其後可以移至其他地方應用,與本來演出動作的演員再無瓜葛。無論是將之套用到角色骨架上,與其他動作契合重組,抑或抽取資料,分析與動作相關的肌肉關節的承重分佈,這種處理正好可以駁入其他範疇,作延伸研究,接向醫療、軍事、電子遊戲、商業空間設計等應用,因而別具商機。
動作捕捉需由演員完成,他們的身影臉龐最終卻會隱去。其中一幕,Pantarey將攝影棚改建成大使館的樣式,拍攝恐怖分子及反恐部隊的攻防實況。拍攝期間,場內鴉雀無聲,雙方陣形各自目無表情地演出攻堅防禦,生死如一,動作之間也無連貫。新入職的員工質疑,這種表演並非演出,演員卻表示,自己的畢業論文正是研究德國表現主義,默片中那些扭曲臉容以表達情緒的演戲方式。問及他有否於當代劇場出演,他就表示:「當然沒有了,那些自然主義的垃圾——彷彿整個二十世紀從未發生。這裡,這裡才是事情發生的地方。這才是真實所在。」於是,動作捕捉中模擬真實,予以模型的做法,成了小說的一大主題。一如《化身》中主角那艘虛擬的太空船「遠星號」(Sidereal),名字實指與星體相關的計算,驟眼看去卻似是與現實平行的另一世界(side-real)。由是,小說拋出的問題即是,有了動作捕捉之後,動作究竟有何意思?假如現實世界狀似要被平行的虛擬場域侵入取代,兩個世界之間的互動又是如何?
截取動作的方法
同一時間,一家匿名公司也委託了法律事務所,為他們研究將動作本身註冊版權的可能,期望在人機互動的後續發展上尋找投機機會。在版權法上,完整作品容易定義,而單位(如字母、音符、筆觸)則難以受版權保護。手勢及動作恰巧墜入難以判斷的位置,無法清晰地界定,截成一個個系列。因此,他們需要尋得法律上的先例,讓人可以定義動作。法律事務所的員工之一,就從莉蓮・吉爾布雷斯(Lillian Gilbreth)的時間與動作研究(time-and-motion studies)中得到啟發,並由老闆指示繼續研究。
吉爾布雷斯的時間與動作研究,主要用於工業方面,承接泰勒主義的「科學管理」方法。泰勒認為,工人時常偷懶,需要嚴格管理,消除浪費,而吉爾布雷斯則循工人的疲勞入手,認為有一個「最好的方法」(The One Best Way)去進行重複性工作,令他們保持健康,同時提升效率。為了研究工人的動作樣式,她與丈夫發明了一套方法,為工人戴上發光的戒指,以長時間曝光的方法,研究手部畫出的軌跡,一種光的書寫。軌跡的長短間距,可用以調整工人的工作環境,比如抬高工作枱,縮短貨物搬移距離等,改善效率及疲勞狀況。有了最佳的動線,吉爾布雷斯就會製作一套金屬模型,讓其他工人都可以按鐵軌的彎曲路線,學習更有效的工作方法。法律事務所認為,這種金屬模型正好充當先例,訂明一個動作系列的起始與終結。因此,小說中對動作的定義、研究及處理,不僅關乎科技發展,同樣涵蓋法律上的探索,牽涉商業法的權力。
有趣的是,整部小說所展示的人物角色,幾乎全是在工作時間中度過的,所有行動均按其專業身份進行,與個人幾乎無關。這不是說,他們並不享受,相反這些人物似乎都對工作抱有熱誠,一直各有啟發。一如動作捕捉演員所言,麥卡錫一直堅拒自然和寫實主義,無意處理角色的內心發展,於此更將焦點放入公司之間的合作與競賽,比起人物塑造,他更希望處理由動作捕捉所衍生出來的,將真實重寫成虛擬的基建系統問題。
以真實為據的虛擬性
由於小說以動作及時間為主題,整部作品對動作的形容鉅細靡遺,常會精細至關節和肌肉的發力順序。小說首個動作捕捉實境中,Pantarey在攝影棚中置放軟床,邀請一對男女在床上交合,試行各種姿勢。不過,這一場模擬卻非為製作性愛場景而設。整場試驗希望測試的,是異性性交的多重姿勢,究竟會對股骨、髖臼及關節施加多少壓力,研究結果將有助經歷關節置換術的患者重獲性生活,兩位替身將會「為無數的婚姻承保,為無數的重新結合承保」。於此,兩具真實的身軀,以一次替換過程,經由傳感器的轉譯,化身數據,為其後千萬位患者提供繁衍/複製的基礎。
其後,在電影《化身》的中段,有一段場景講述劇中兩位主角誤服春藥,在無重力的環境下瘋狂交合。為了模擬這段經過,電影公司聘請了業界頂尖的動作捕捉公司處理,卻發現真實的身軀處處下垂,即使以鋼線操控身體,額外以繩索拉扯下垂的部分,看來也只如繃緊的雞皮,場面結果「如同地震時的肉店櫥窗」。最終只能以前述的性愛數據為基礎,從身體相觸時的動作,再行延展出離開的動作,模塑出無重力狀態下,激情澎湃的完整場景。
由此,麥卡錫描繪出真實與虛擬之間曖昧的關係:虛擬試圖指向某種可複製的完美形式,卻必須以真實之物奠基,並無完美之姿。按他所言,當前的世界「有一組捕獲機制,將物化作數據的機制——而在這套機制的正中央就是身體,身體的物質性。」^3 物質在此處正是完美形式的破敗因素,偏又是它賴之而生的起因。
虛擬下的記憶與時間
一個受虛擬所伴的現實,對個體來說究竟有何影響?
小說中,Pantarey公司有一位實習生,由於經驗尚淺,需由正式員工帶領,了解公司的廣泛業務。其中一次,實習生與上司坐在咖啡店門外,打開手提電腦,透過街角上安裝的攝像頭,觀察人流走向的隱藏節奏。上司以離散時間馬可夫鏈吹噓,指出這種事件鏈的特色就是無記憶性,期後將會發生什麼事件,與之前曾經發生的事情無關,滯後現象(hysteresis)不會出現,只會按當下的情況,決定之後的隨機走向。
實習生開始走神,眼睛看向街道,一如佩雷克(Georges Perec)《窮盡巴黎某地的嘗試》,注意起路邊走過的人、地上的石頭、陽光的照射方向⋯⋯她明白現在的工作,就是提煉群眾的行動模式,之後會有多重應用,產出演算法,在電影、遊戲中模擬人群的走動,她卻隱隱覺得,當下的境況,已由某種演算法所定斷,人物的節奏早被模塑。她突然有了雙重視角,一個從她個人出發,另一個則是由上而下的操控視角,將眼下的空間劃分成格,動作繪成各種移動樣式。單是這種雙重視角的入侵,已叫她回想起早前觀看的,士兵遙距操作無人機執行轟炸任務的記憶,將之嫁接到這個空間之中;換言之,僅僅認知自己有這種視角,就彷彿已在對這個空間施行暴力,幻想的轟炸場景降臨街道,使她恐慌發作。
實習生的身體經驗,恰巧說明了小說當中,個體與模型的對立。Pantarey的研究工作,包括個體的肢體動作,以至群體的行動樣式分析,以此獲得的知識,其後就可以變成某種暴力,甚至單是認知已足以延伸構成暴力。在電腦及鏡頭的分析下,事件的發生顯得只餘特定模式,偏偏人具有記憶,每一動作皆由自身出發,受制於先前的因素。於此,分別正在時間:電腦分析所理解的時間,無非可以重複、可供預測的時間截段;個體所理解的時間,卻從記憶開展,連續而延綿。實習生所體會到的暈眩與恐慌,既是由於這兩種時間互不吻合,更是出於虛擬所帶來的分析模型,更動了現實的地基,以致人在其中只如玩偶。既是如此,這種覺察就忽爾提升,毀滅的影子如鬼魅降下,衝擊了生命的實感。
成像時間,時間成像
處理好劇情上的麥高芬之後,小說最終回到電影《化身》的終幕上。遠星號帶着一眾船員,自殺式衝過恆星,重力、電漿與輻射逐步將整艘太空船解拆,部件橫飛,誘發連鎖效應,終使飛船歸入虛無。電影製成一刻,即是破滅。
電影的電腦合成圖像,場面浩大,牽連諸多系統,需要大量時間運算繪製。《化身》總共44928幀圖像,由電影製作公司的成像農場處理,每一幀需時約62分鐘,處理器可平行同時處理23幀,共計即是逾二千個小時,全天候無間斷運作,成像總時數預計為十二星期,而且只會不斷延長。這些巨量的資訊,每秒湧入,卻必須有一位雜務人員(render wrangler),專責監察成像過程,分配處理器負荷,檢視影像有否出現瑕疵,將出問題的圖像發還重做。一如肉身與虛擬的關係,縱使科技有多複雜,人總在其中一環:「帝國會崩潰,死星會爆破,四出奔走的雜務人員卻始終在此。」雜務人員置身影像製作的流水線,受數據流一直沖刷,電腦與他體驗的時間的巨大差異就在此開展:屏幕上的影像僅只一瞬,卻需要逾一小時的處理,時間由此放大,遠超常人體會的規模,一種無法企及的異化時間。
《化身製作記》以破滅為終結,正好完成了一個仔細的解拆過程:一場科幻電影的製作,從動作捕捉、模態分析到影像處理,恰巧指向了動作、身體與時間的異化;現實正經受一場大規模而隱密的替換行動。不過,小說中的角色,似乎並未因異化而迷惘,反而在這些科技場域中,一再找到滿足感。也許,在麥卡錫的理解中,現實受到中介已成事實,懷緬舊日未經玷染的世界既無意義,也不可能;最重要的始終是以小說的方式,去思考這些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新世界狀態,如何從基建上改換體驗。在最好的情況下,一部小說既是一組故事,更是一套觀看世界的方法:《化身製作記》所製作的,正是在重重科技接入之下,你我的肉身與現世。如何能夠在這樣的世界中,研展出嶄新的視角,發掘當中的微妙之處?那或許就是小說的作用了。
(原載《SAMPLE 樣本》第二十九期〈時間電影院〉)